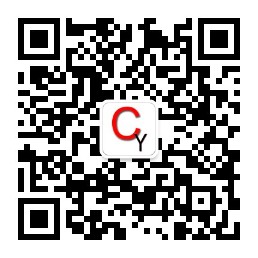随着像贝聿铭(im pei)和凯文-罗奇(kevin roche)这样伟大的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去世,纪念碑性建筑越来越脱离当今社会。
几年前我听过一个关于已故的贝聿铭的故事。建筑师山迪-贝(sandipei),一位贝氏家族的老朋友,告诉我他的父亲去西塔里辛(taliesin wes)的朝圣之旅,就是在我生活和教书的地方,去见弗兰克-劳埃德-赖特(frank lloyd wright)。
贝聿铭开车穿越全国后,他停到了赖特的“冬季营地”,结果赖特夫人的爱尔兰猎狼犬跳到了他的车上,吠叫着,咆哮着。他转了几圈,一直没见到主人。
这似乎是一个相应的形象,让我记住了贝聿铭——一个尊重传统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延续传统的人,但他在如何做到这一点和他的个性上都很谦虚,并且远离对抗。
如果说赖特是散发出魅力,沉溺于无止境的实验,如果说年轻的建筑师们是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,同时反叛他们的先辈,那么,贝聿铭是寻求做一些简单的事情,但仍然渴望有他的建筑特色的建筑大师。
一、贝聿铭尊重传统,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下去
随着贝聿铭的去世,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建筑师,最后一批“现代丰碑”制造者也去世了。一个接一个地,那些通过设计一个精简的模式,更新了为重要机构设计建筑的概念的大师们(都是男性)已经死了。
贝聿铭不仅比他的大多数同辈人都长寿,而且比大多数后现代建筑师都长寿,他们给这项工作带来了更轻松、更不敬的影响。
贝聿铭最好的作品像凯文-罗奇的作品一样,(他先于贝聿铭几个月去世)。它重新思考了“古典纪念碑”的本质——它的正面和平面都是巨大的、雄伟的、层次分明的,由石头等材料和圆柱等元素组成,这些元素超出了日常生活的正常周期。
相反,这些建筑师把“纪念碑”简化成了他们切割、打磨的“石块”。使它们向复杂的社区和场所开放,而这些复杂性超出了该学科传统所知道的如何适应的范围。
在贝聿铭的作品中,金字塔变成了玻璃,不像原来的那样,是一座坟墓,相反,它是一个供大众使用的入口,“纪念碑”的周围可以储存物品。
二、这些建筑师把“纪念碑”简化成他们切割、打磨的石块
约翰-拉塞尔-波普(john russell pope)设计的“高级艺术神庙”——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(national gallery of art)——收到了一份由碎片制成的附加作品,这些碎片突出在一个开放的庭院周围,提供了多条路径,可以看到比主楼珠宝盒更灵活的画廊。
贝聿铭处理“纪念碑”的能力也使平凡变得高尚:他在职业生涯早期为开发商威廉-泽肯多夫(william zeckendorff) 设计的公寓楼变成了坚固的网格。它们站立在曼哈顿的混乱中,像是有人居住的石柱。
他后来的最好的摩天大楼,如约翰-汉考克大厦(john hancock tower),,其主要设计师是他的长期pg游戏试玩的合作伙伴哈里-科布(harry cobb),它变成了一个玻璃棱镜,在波士顿展开它的三角形形状反射和吸引光线。
如果贝聿铭的建筑大多是城市建筑,那么凯文-罗奇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郊区。他能够用中庭和开放式设计打开公司办公大楼,同时将联合碳化物公司(unio n carbide)等公司的建筑打造成巨大规模的现代帕拉迪奥(palladian)别墅或庙宇。
他的小型艺术建筑,如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大学(wesleyan university)的艺术学院,像贝聿铭的建筑一样支离破碎,但又像贝聿铭的建筑一样坚固,效果也一样好。他的福特基金会大楼(ford foundation building)在纽约挖空了这个宏伟的机构,给了它一颗“绿色的心”(green heart)。
贝聿铭和凯文-罗奇的作品,以及欧洲的阿尔多-罗西(aldo rossi)和日本的丹下健三(kenzo tange)的作品,都是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“纪念碑”解体的纠正,也是对新野兽主义(new brutalism)的沉重保护。
融合一种认识,即我们需要某种比生活规模和设计都大的焦点、锚定点和社区中心,以及一种认识,即我们也希望这些建筑向我们所有人开放,不管我们的文化背景、才能或品味如何,他们都使用抽象化和碎片化策略,来达到显著效果。
然而,他们所没有做的,是创建一所学校,或者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之外对学科产生影响。在许多方面,他们的作品是路线的终点,在现代性晚期的丛林中留下了废墟。他们不教书,也没有多少人试图模仿他们的设计。他们也变得过时,到了千年年底,他们的许多业务委托都已枯竭。
凯文-罗奇试图通过对后现代影射的不成功突袭来反击,但贝聿铭却退缩到了为中国苏州设计小型博物馆等建筑“珠宝”的制作中。每一个都是独特的和无可挑剔的细节,在规模上是微妙的,但在效果上却令人印象深刻。
贝聿铭也比几乎所有的下一代人都长寿,他们以异想天开、富有表现力的形式,甚至以更进一步的分裂来回应这些认真的努力。
最近,我们失去了斯坦利-蒂格曼(stanley tigerman),他的无所顾忌掩盖了他在建筑中——从盲人图书馆到大屠杀博物馆和纪念馆,对严肃形式、计划和意义的奉献。
三、建造“纪念碑”的想法似乎过时了
贝聿铭甚至比普利兹克奖得主第一人——菲利普-约翰逊(philip johnson)活得更久。
那么,贝聿铭和凯文-罗奇等人的遗产是什么呢?当然,白人统治这个职业的时代应该结束了,尽管这个时代似乎仍坚持着一种既令人惊讶又令人不安的坚韧。当然,建造具有持久性和吸引力的“纪念碑”的想法似乎和“大帐篷政策”政党或既定宗教一样过时。
在一个不断变化、分裂和怀疑的世界里,我们应该关注pg游戏试玩的文化,并且它们应该代表那些持久的价值观,因此它们的终点应该是“纪念碑”,这一想法似乎很难得到捍卫。
史蒂文-霍尔(steven holl)、托德-威廉斯(tod williams)和比利-蒂恩(billie tsien)、弗兰克-盖里(frank gehry)、彼得-卒姆托(peter zumthor)和矶崎新(arata isozaki)都是一些仍然活跃的设计师,他们正在努力保持这一传统。但是,无论从字面上还是比喻上讲,由于需要开放和多元化,由于受限制的预算,也许还有他们自己缺少自信,他们的建筑都被割裂了。
无论是国家美术馆(east wing of the national gallery)的东楼、纽约大学的教职员工宿舍 (new york university faculty housing)、博尔德市外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(atmospheric research)或苏州博物馆(suzhou museum),站在贝聿铭这些最好的建筑物前面或里面,都会怀念这样熟练的设计,而留下接受和庇护我们所有人的建筑的能力。
我们只能希望新一代的建筑师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学习贝聿铭,设计这样的现代建筑,即使它们看起来或运作不像“纪念碑”建筑,也配得上这个名字。
本文作者介绍:
艾伦-贝斯基(aaron betsky)是塔里辛(taliesin)建筑学院的校长,艺术、建筑和设计批评家,著有十多本关于这些主题的书籍,其中包括即将出版的《建筑和设计中的现代主义》一书。他为建筑杂志网站《建筑之外》每周两次撰写博客。
艾伦-贝斯基曾在耶鲁大学学习建筑和人文科学,曾任辛辛那提美术馆(2006-2014年)和荷兰建筑学会(2001-2006)主任,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(1995—2001年)建筑与设计策展人。2008年,他还执导了第11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。